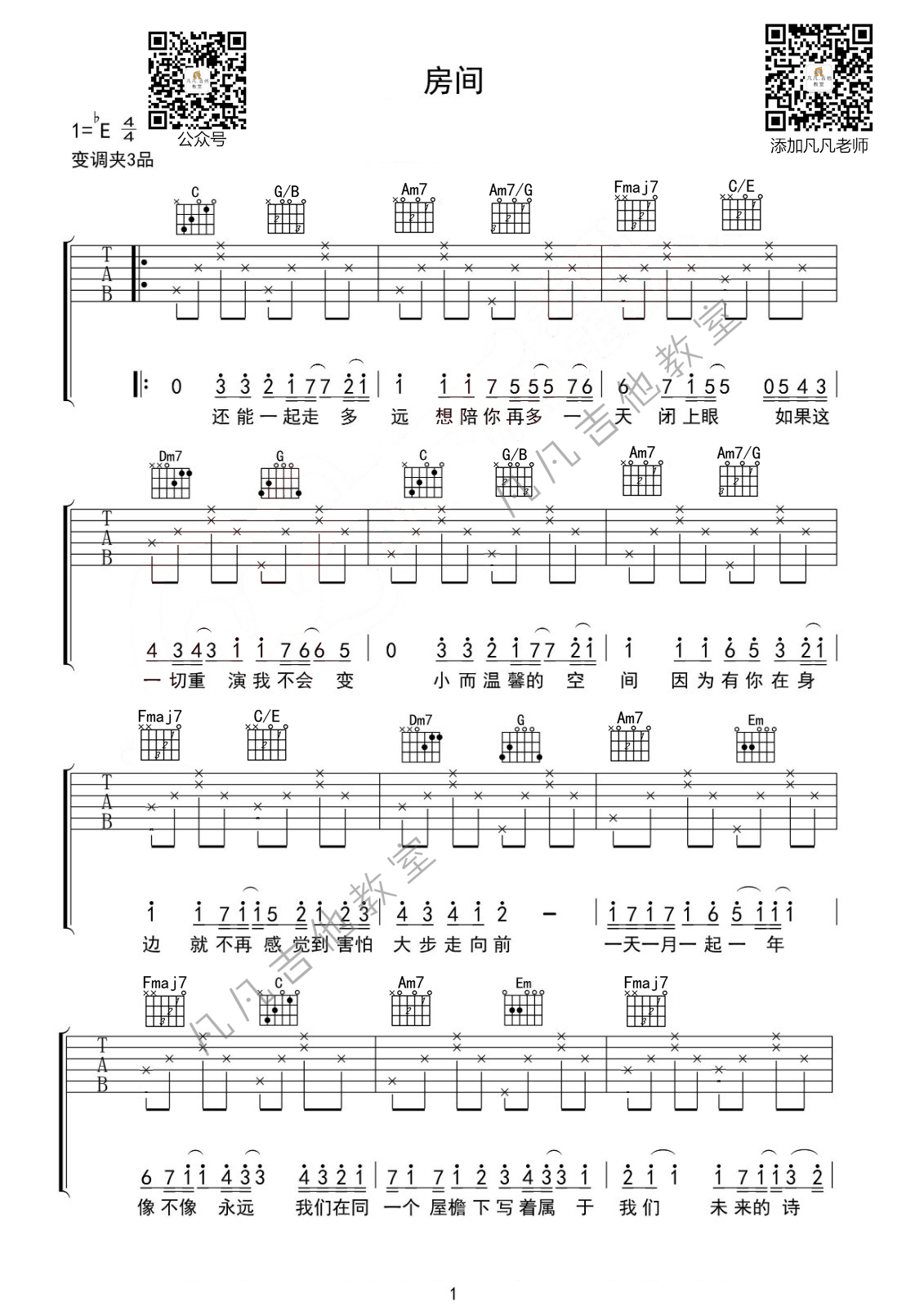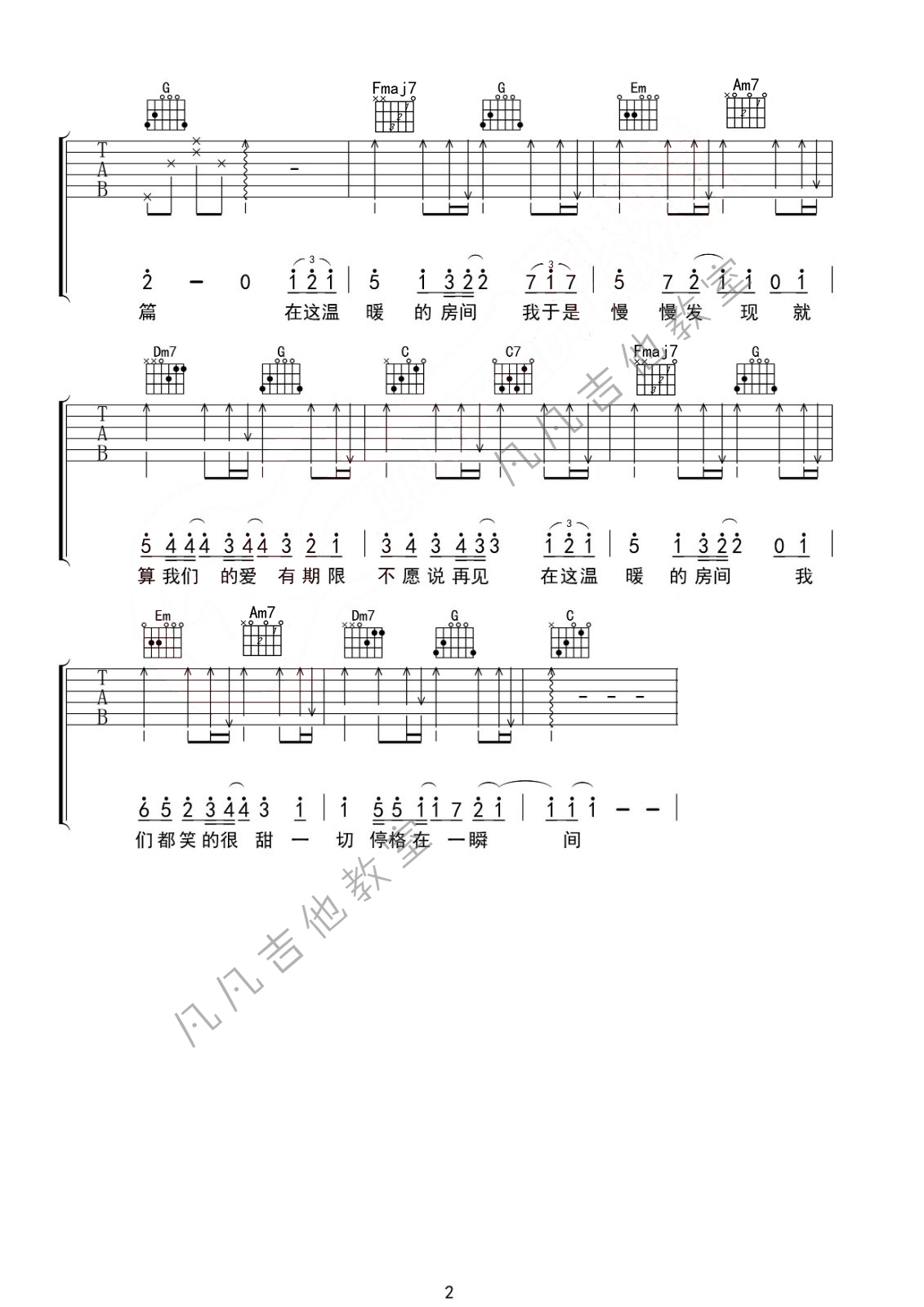《房间》以私密空间为载体,通过具象的日常物象构建出深邃的情感图景。墙上的水渍、未拧紧的水龙头等细节成为记忆的锚点,将抽象的时间流逝转化为可触摸的存在痕迹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门"与"锁"构成双重隐喻,既是物理空间的隔断,也象征着心理防线的建构与瓦解。光线的明暗变化暗示着记忆的选择性留存,那些被阳光晒褪色的角落,恰如被时间冲刷后依然顽固的情感印记。抽屉里未寄出的信笺和衣柜深处的樟脑丸气味,共同编织出关于等待与腐朽的辩证叙事,展现保存与消逝的永恒角力。歌词通过空间静物与动态时间的对抗,揭示现代人孤独的存在困境——在有限物理空间里试图安放无限的精神漫游。时钟嘀嗒声与水管渗漏声形成的错位节奏,暗示着个体时间与社会时间的永恒不同步。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悖论式生存状态:越是精心构筑的封闭空间,越暴露出内心难以填补的虚空,而正是这种自我囚禁的清醒认知,反而成就了某种残酷的诗意栖居。